傅聰因得新冠肺炎在英國離世,殊為可惜。
傅聰無奈逃脫當年中國的黑暗,卻逃不脫今天的病毒。
在微信上一篇悼念傅聰的文章中讀到:「……周巍峙請傅聰吃飯,詢問有什麼事需要幫助。傅聰說,黃賓虹送給父親的書畫,他想帶幾幅去英國,海關不准。周巍峙於是同外事部門聯繫,使之放行。」
黃賓虹是現代畫壇上的巨擘,他的《黃山湯口》巨作,在二零一七年的嘉德拍賣會上,曾以三億四千五百萬人民幣的高價落槌,驚爆拍賣市場。黃賓虹的畫作,以焦墨著稱,畫法高古,所以能看懂者不多,有些人認為他的畫有「野氣」,不入流,以致他五十年代初,賣畫不繼,生活困頓。那時他常以畫作送人,送給能欣賞他作品的知己,其一是裘柱常,他是《黃賓虹傳記年譜合編》的作者,夫人顧飛是南匯人,黃賓虹的學生,翻譯家傅雷的表妹,也是女子書畫會的幾位才女之一,早年曾跟江南名士錢名山先生學過詩詞。由她的介紹,使黃賓虹結識了傅雷。
黃賓虹不得志的時候,曾自謂:「五十年後人們才能懂我的畫」。不料留學過法國的美術評論家傅雷,卻提前了五十年看懂了他的作品,成了他高山流水的知音,視為知交。為此他留下欣喜的文字:「此(傅雷)亦鄙人知己,至感似較黃大痴(黃公望)自言五百年後必有知者,吳仲圭(吳鎮)自信數十年後遂不寂寞,抑又勝之。」 相知之樂,溢於言表,這從他兩人的通信中也可以查得,傅雷向其索畫,黃賓老無有不從,每逢時節送上得意之作。傅雷家藏有不少黃賓虹的精品,為業內人所共知。
文革抄家,傅雷所藏黃賓虹字畫,全數沒入官府,經過挑選,進入上海博物館深藏,秘而不宣。
八十年代,政治氣候比較寬鬆,上海博物館舉辦了一次《黃賓虹畫展》,展品中有不少傅雷上款的畫作,朋友見了,告訴傅雷的次子傅敏,據說傅敏前往催討,但人微言輕,懇求無果。等得傅聰回國,一經向統戰部提出,上司一紙屁(批)文,上海博物館立即執行,遵令悉數發還。
嗚呼,傅家意外有幸,因為有叛國投敵犯作為統戰對象,名聲大,所以抄去的字畫,可以完璧歸趙,至於沒有叛國投敵犯的家庭,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卻說這次畫展,不慎泄露了天機。就此,上博內部的藏品名冊上,出現了「絕密「字樣,上款有名字的字畫一律不准出展,更不許外人調看。據筆者所知,李秋君就藏有許多張大千的精品(有目睹者說,見過一幅張大千的四尺工筆《駿馬圖》),和兩人同是五十歲,作」千秋百歲「壽誕時的畫作。李秋君終身未嫁,身後無嗣,被抄去的東西無人領取,成了「國貨」,至今不知落入誰手?據說其中還有一套純金的十八羅漢。
前些年手機上微信的信息量大,有關方面,來不及屏蔽,漏出了不少七十年來,殺戮地主搶奪土地,批鬥資本家掠奪工廠,驅趕城市平民,強拆民房的真相……但像《紅樓夢》中賈雨村幫賈赦強奪石呆子扇子的之類的故事尚還少見。
說完上面的故事,順便再聊一下我聽聞的有關黃賓虹作畫的軼事,雖是離題,卻也有趣:
八十年代我出國前,經常出入於巨鹿路「莊暮堂「,聽謝老講述前輩畫壇的故事,一次他談到黃賓虹,說黃賓虹很吝嗇,你坐在他旁邊看他畫畫,坐一天也不會請你吃飯,他自己肚子餓了,就從衣袖裡掏出棗子和柿餅充飢……陳佩老也說,她跟隨黃賓老多年,說黃賓老作畫前喜歡把墨塊浸泡在小酒盅里,然後在宣紙上塗圈圈,說在畫太極圖,然後用脫筆作皴。他的畫案旁,有一隻竹編紙簍,他把畫好的畫丟在簍子裡,你要跟他索畫,他會說自己到紙簍子裡去揀……記得那天陳佩老說這段故事的時候,情緒特別好。
回頭還再說傅聰,很可惜,他逃過中共的第一劫,卻沒有逃過第二劫。但願他去到沒有恐懼的世界裡,聆聽父親傅雷暢談:「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第四才做鋼琴家……」的教誨。也許此刻他倆正在談論:藝術、文學、繪畫、音樂……以及在祖國人間陽光下不便說的真話!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於食薇齋北窗下
本文由看新聞網轉載發布,僅代表原作者或原平台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看新聞網僅提供信息發布平台,文章或有適當刪改。
本文網址:https://vct.news/zh-hant/news/6e35146c-967e-4d3a-90a8-2b8377750b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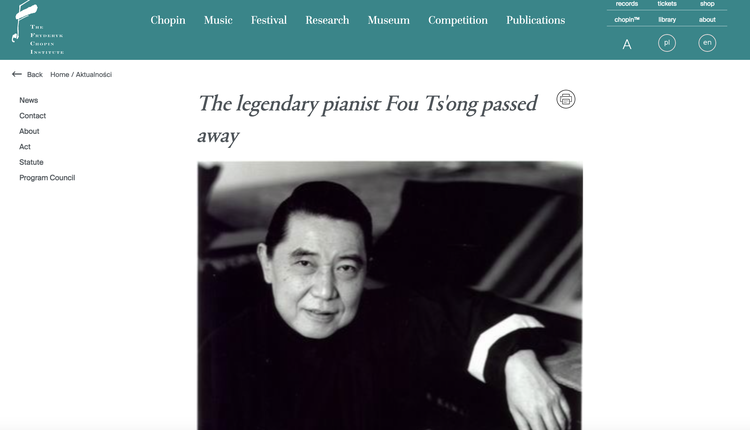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