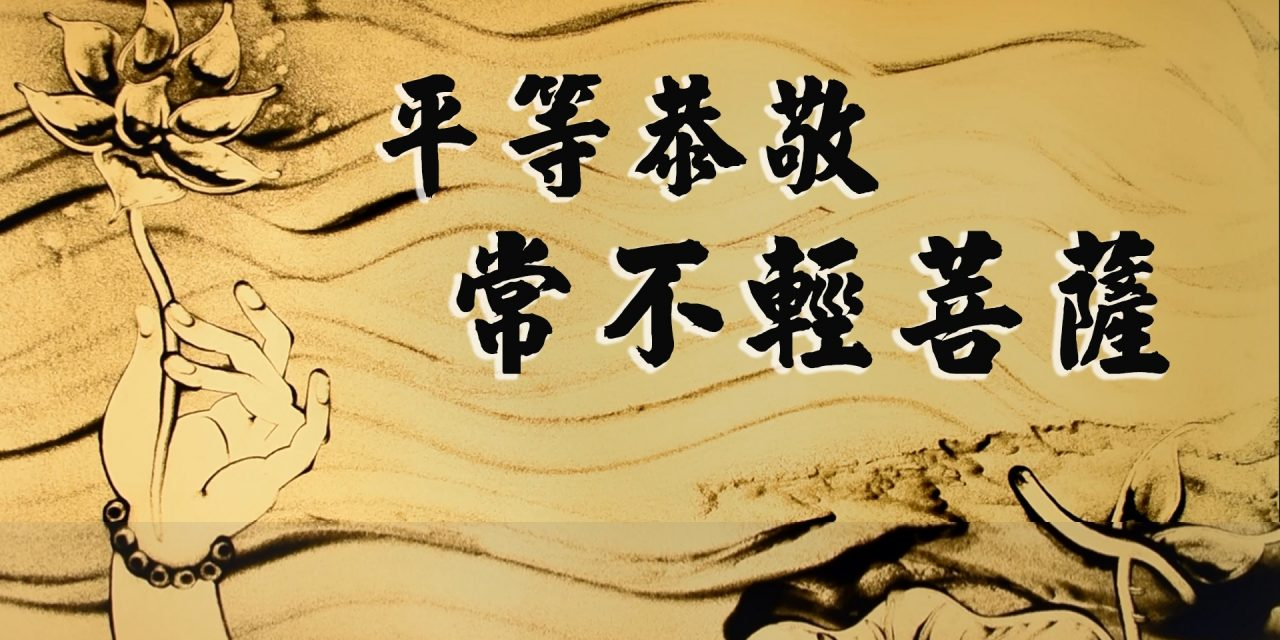拿了合同纸,到工业厅属下的原料局签名领取铁枝,管理的干部看过证件纸张后;要元波先去银行提取原料的钱,先钱后货,是他们的规定。
第二天、银行职员拒绝付款,要元波出示原料已妥收的单据,银行的原则是货到付款。那些存款是九龙工厂的资金,九龙厂的经理黄元波无权支取用以付款提货,(西方的读者们是不能想像自己的存款不能提取的怪现象;但在共党制度中的计划经济,钱是你的,但对于钱的应用却要他们支配,这是千真确的事,不是神话)。
元波再回到原料局,要求他们先送货,并出示了存折,证明了银行存款足够支付货款有馀,但局里的共干绝不肯破例。
第四天他到工业厅,把困难向上报告,得到指示要他到胡志明市银行(前西贡银行)请那边的同志写介绍信。
拖了整个星期,原料仍无著落,元波终于到了西贡。胡志明市银行的越共满脸笑容的听了他的遭遇,对九龙产品深感兴趣。元波早学乖了,立即答应另日奉上三对样品,换回了一张解冻存款的证明书。
原料终于运到工厂了,明雪的脚伤已痊愈,又再上班。可是、火炉组的弟兄们并不能开工,燃料煤炭仍没运到九龙的货仓。
再奔走了四天,五吨煤块才倒进火炉组的燃料货仓里;技术科的车刀、钻头、磨石、皮带、每样都按著配额向有关部门购买。有了这样却少了那样,整间工厂少了车刀、车床部门的技工唯有到对面九姨咖啡店里下象棋。幸而合同订单不能完成,竟还可以得到竞赛超额生产冠军。这点奇迹,元波如非亲历,他怎样也不会相信的。
三月间工业大会是在郡址举行的,工业局长在致开幕词后,就分别进入对全郡工业进展总结报告;九龙厂是郡出名的冠军厂,所以元波备受注意。在大会上轮到他演讲时,他从容的站到麦克风前,先向留著山羊胡的胡志明遗照及金星红旗鞠躬。内心有虚与委蛇无可奈何的一份假意,头也就点到有些勉强。然后面向听众,用纯正南方口音的越南话发言:
“局长!郡长!各位贵宾,各位同业先进朋友们:
我首先代表九龙工厂的弟兄们热烈祝贺大会成功。感谢工业厅的首长们给我这份荣幸向全郡的工业同行先进朋友们讲话。
九龙厂自去年创办后,全厂弟兄们以革命热情和奋斗意志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予的任务。我深深感谢工业厅的有关干部们给予的热情支持。
从经验上,容许我坦白说,许多不应发生的困难和不合理的延迟工作进展;使到工厂每年只能生产八个月的开工率,那种缺点其实都可以改良和克服。
各部门机构似乎没有规划一致的行政律,我领购原料铁枝及煤炭所奔走的部门多达十二处,总共花费了十二、三日。市场上有很大的需求,可是我却限于合同计划,让弟兄们无所是事,机器冷却停顿;同胞们没法购到迫切替换的单车零件,这是很痛心的损失。
我和工业厅的干部们反映,他们却说这是‘社会主义优越的计划经济’,我不了解那些高深的理论。只是把从处理工作上所遭遇的千奇百怪的现象,忠实的在大会上提出;盼望有关的各部门能够改良,那么、相信工业的前途才会更进步和才能生产足够同胞应用的民生必需品。
谢谢大家!”
热烈的掌声在会议厅里回荡,出席的干部越共们却目瞪口呆,议论纷纭,许多来参加开会的工厂主持人都跑来和元波闲谈。
翌日、中越文两份报章发表的十一郡工业大会报导,竟完全没有提及元波演讲的新闻。
吃早餐时,婉冰有点不安的说他:
“你怎么还是那样老天真?祸从口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那班人不犯你,你应该庆幸了,居然胆敢讲他们的不是。唉!我真担心呢!”
“别大惊小怪,我实话实说,好意提出改良的见解,又没有骂他们。”
“他们难道不知毛病在哪里吗?要你多嘴!”
元波心里有气,再加上婉冰语气中浓浓的怪责意味,竟把声浪扯高:“不和你辩这些了,有事、反正不会拖你下水。”
“阿波,你吃错药了,夫妻是同命鸟,你有事我就会好过吗?”婉冰语气平静的说。
“对不起,没什么事的,你别胡猜,我上班了。”
元波放下碗,推开桌旁的报纸,拧拧明明的小脸蛋,又亲了阿雯,吻了阿美的前额,和妻子挥挥手,才出门去了。门外街角处,几个陌生人,早已在等待他了。
九龙工厂一反往日的吵杂,没有机器开动的声音,元波停放好脚踏车,走进去,立即给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厂地中央变成了个临时会场,弟兄们都坐在地板上,办公室里几张台和饭桌,移在靠墙处,搭成了个讲台,墙上用粉笔涂满了打倒资本主义美伪走狗帮凶等充满火药味的口号。
有好多句居然指名道姓的要打倒黄元波,他心惊的瞄到那些口号,本能的想退出去;没想到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公安部派来的公安秘密探员,面无表情的挡著去路,把他强迫到讲台上。
嘘声响起,由一个工团干部带领,其馀的人跟著 喊:
“打倒资产买办美、伪帮凶!”
“打倒九龙工厂的仇人!人民的公敌!”
在一片打倒声中,元波脸色青白的往下望,明雪也在场,独独不向上看元波。这时,厂里的技术组长阮拾走上台,指指元波说:
“弟兄们,他是美伪集团的帮凶,剥削了我们全厂工人,没有参加直接劳动,满脑子都是些污秽的念头,破坏了革命政权的政策,污辱了英明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时刻在想著资本主义的垄断经营法。这个人,再也不配当我们的经理,打倒他,打倒我们的剥削者。”
阮拾越说声浪越高,四面八方随著他高呼的音波起落,“四面楚歌”这句成语像电流似的在元波脑中闪过,直到这个时刻他才深切了解这句形容的内涵。他原来站立著,一脸悲愤的面对审判他的人群。
这时,两位穿黄制服的公安,野蛮粗暴的一起行动;把他推倒在台上,其中一个恶狠狠的指著他的前额大声叫:
“他是破坏革命的美帝走狗,公开对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作胡乱而不负责任的恶意批评,胆敢诽谤我们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心破坏我们全民的革命成果。是不是 ?”
元波茫然的看著他,心中此时终于明白了,一般寒意也自背后爬升。他忍著,轻轻的咬紧下唇,不让自己出声。寒意里也揉杂了一腔怒气,假如开口,一定会把丹田中的气迫成杀人的声波,把面前这个共产党徒震死。
“用钱收买各级的忠贞同志,要想使我们的革命热情冷却、变质,是不是 ?”他呐喊著,忽然又指著台下的明雪说;“你乱搞男女关系,多次试图非礼美丽的女秘书,厂技术组长及弟兄们都亲眼看到你天天送她回去,是不是 ?”
元波猛然仰起头,惊异而怨愤的想张开口申办,不意明雪比他快,站起身很生气的对著台上吼:“你乱说,波兄不是那种人。”
“住嘴!你这个婊子。”穿黄制服的公安用更大的怒吼指著明雪,然后又叫著:“把这个反革命份子也拉上来一起审判。”
台下的越共便衣立即到明雪身边,刚要伸手,明雪狠狠的摔开,自己上台去。
元波很感动,再也忍不住,张开口对他们大嚷;“不关她的事,放了她。”
那个主持斗争的工团头子首次出声,指著来到台前的明雪:
“你丈夫是美伪空军上尉,双手染满了对祖国人民的鲜血,你不知对革命政权悔改,竟也连同这个吸血鬼来对付人民政府,嘿!嘿!。”
明雪蹲下来,移近元波,双眼勇敢而不惧的望著他;千言万语都在温柔的目光里,像个打开的久闭门窗,急促的呼吸新鲜空气;往外看风景不变,往里瞧,布置也依然,只要瞄一眼就够明白了。
“雪!你为什么要这样傻?、、、、、”元波感动而温热的说,声音很低沉,几乎是不能傅达的微弱音波。但明雪己经听到了,只对他点点头,展露著凄凉寂寞又无奈的微笑。然后便低下头,什么也不看,文静而安祥的蹲著。
“无耻的狗男女,还不认罪,如没私情,为何要替他申办?”
“我们是清白的。”明雪狠狠的吐出一句话。
“哈!哈!你们相信吗?”工团的头子招招手,外边走进几个穿黄色制服的公安,不由分说的把明雪强拖出去。元波本能地想伸手去拉她,一个公安拿起手上的木棍当头打下;元波一阵昏痛,连叫喊的声音也发不出来,神思恍惚的看著明雪消失在厂外。
接著许多咒骂声音又在他耳际回响,他迷茫里想起了父亲以前提及中国共产党土改时的公审,没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完全是野蛮式残酷的迫打成招,竟然是千真万确的在这里重演著,而且主角是他自己。难怪呵!越共死去的头子胡志明会那么亲热的把中国看成“同志加兄弟”,原来完全是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里,整套方法照搬来用。
矇眬里,元波忽然被一阵刺痛惊醒,那个恶狠狠穿黑衣的工团领导把几个啤酒瓶打碎后的玻璃碎片,平均散在台上。两三个手下硬迫强拉地把他按倒跪在破璃上,鲜血和强忍的泪水都一并流泻涌现。
“走狗越奸,你认罪吧!”一个越共指著他吼。
那些陌生的脸孔,那些穿公安制服的人,热烈的响应。九龙厂的弟兄们目瞪口呆的看著这一幕令他们心惊胆跳的斗争大会;许多平时和经理私交颇好的工友,不想也不忍看下去。可是、又没勇气站起来离场。像小时候聆听鬼故事,心中很怕;但又相信自己一旦走出门外,那些阴魂鬼怪就会缠上来索命。唯有哆嗦著留下来,听到口号,在那些工团狠狠瞄射的眼光下也不得不跟著高喊:
“你认罪吧!你认罪吧!”
听音像潮水,一波又一波的涌进元波的耳膜,他无力而清醒的在狂潮的冲击中摇著头;迷糊的神智中,他又听到了掌声、欢呼,然后他就被许多人拖拖拉拉的拥上了一部公安车。
以为送去枪毙,以为送去监狱,以为从此再见不到妻儿子女。元波愤愤不平的仰望悠悠白云苍天,在心底狂呼:“天啊!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车外,白云不飘,苍天无语。公安车紧急停下的地方,没想到竟是他以为今生再也见不著的家了。一阵冲动,眼眶潮湿,噙著的泪水又模糊了他的视线,有如孩子在外打架,输了跑回家扑进妈妈怀抱里,才把委屈受辱的泪痛快的泻出来。
两边膝盖所粘刺的碎破璃在车上时己用手拔出,斑斑血迹凝固成一层褐色染透裤管,分外瞩目。踏进家门,他无力举步,几乎摔倒,幸而前后四五个公安围绕著他,见他摇晃著上身时立即双双伸手扶持,半拖的把他拉进去。元波挣扎著把身体移到厨房,看到椅子,一屁股的立即坐下。从楼上走下来的竟然是保长阮文协和另一位公安人员,元波到此刻才大吃一惊的,心里万分强烈的渴望看到婉冰和儿女,他张口问:“我太太和子女呢?”
没有人回答他,送他来的五个人和保长交待几句,留下两个,其馀的就走了。
“你己经是人民政府的囚犯,现在交由我看管和审问;不能离开这个厨房,不能发问。”阮文协洋洋得意的对元波呼喝,元波望著他,这个梳著平头,国字口脸,左眼上有块枪伤把半边眉变成寸毛不生的疤痕,五官因而变得令人有份邪气感觉。讲话的时候,拉动肌肉线条,完全是个丑陋的面谱。啊!这张面谱一向都是笑吟吟的,今天、终于呈现了他的真容。
“人民政府会很宽容的对待知道悔改的人,你的合作,你的诚实将有助于对你减轻刑罚。现在,你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记录下,作为人民法庭上的供词。”阮文协滔滔不绝的说。元波闭上眼睛,把丑陋的容颜赶离瞳孔,想起妻子和子女,他又张开眼,忍不住问:
“保长,我的太太和子女呢?”
“拍!”一个清脆的耳光出其不意的由阮文协快速举手里完成。元波脸上热辣辣地,居然连痛的反应也来不及感觉。
“你无权发问。”出手打人的保长官威十足,元波怎样也不能相信第一次代表“革命”政权到民居探访的那位地方官,就是今天这个土匪般凶狠的越共干部。
明明的哭声忽然从二楼傅下来,元波心里一喜,太太儿女原来被拘禁在楼上。夫妻是同命鸟,自己有了事,做太太的果然不能置身事外,婉冰真是看得很透彻啊!心灵的内疚和肉身的痛禁交并煎熬著他,他真的想冲上楼,热烈的拥抱妻子,伏在她温柔的怀抱里求她原谅。
“你剥削人民的财产,变成礸石或黄金,存放在那里?”
“、、、、、、”元波再次闭起眼睛,也闭起口。
“你保险箱里早先拿走的美钞、黄金片,如今存放何处?”阮文协猛吸一口烟,出劲的把烟雾往元波脸上喷。
“、、、、”元波心里想,原来银行己经把空箱存放文件的档案通知了他。
“你不合作,你是会后悔的。弟兄们,全面寻找搜索这个越奸反动份子的一切非法财产和证件,不要放过屋中的每一寸地方,每一块砖头呵!”保长发出了命令后,丑陋而凶恶的面谱随而匆匆上楼,留下一个手持 AK步枪的越共看守元波。
搬动家私的声音和凌乱的脚步声传进耳膜,元波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土匪”在他家里掠夺抢劫?
午餐时间早己过去,傍晚时分,阿美傻愕愕地充满恐惧的神色自楼上走下来。见到父亲,叫了一声爸爸后,泪水便滚落双颊,然后怯怯地偷瞄一眼持枪的越共,什么话都不敢多说,自个儿去洗米煮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