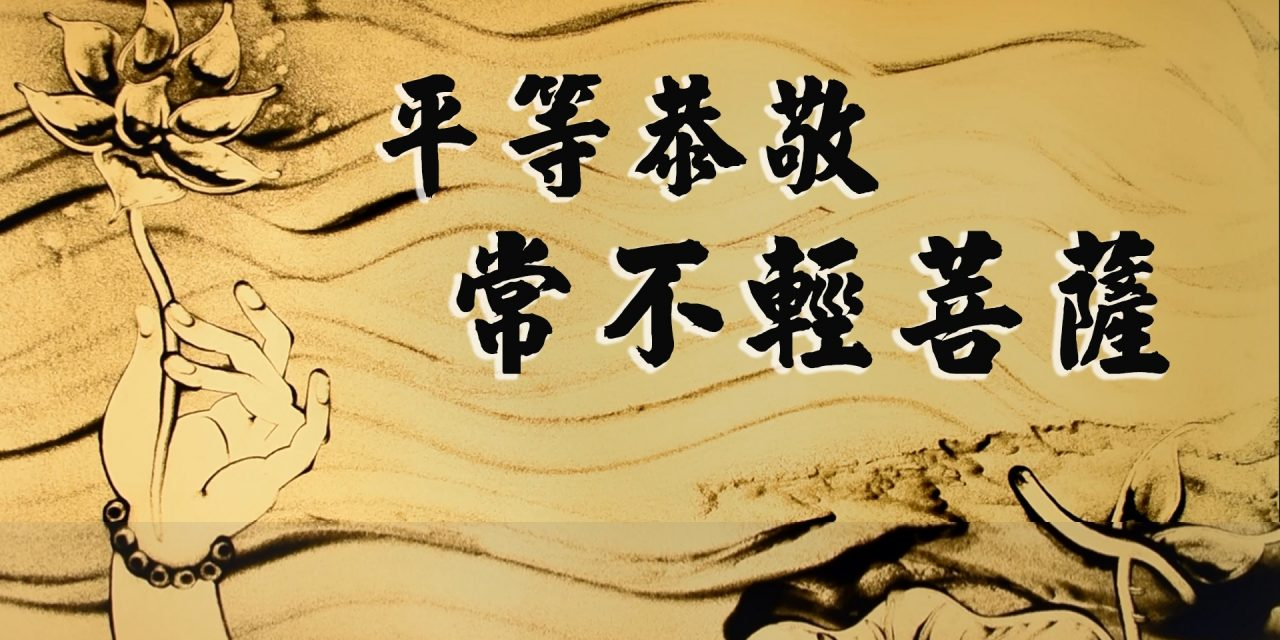农历年底在墨尔本东南区史宾威市、由该市亚裔工商协会主办的庆祝新年年市,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个族裔人士。我徘徊于各式越食摊贩前,让鱼露芬芳的气味治疗我浓浓的乡愁。
在卖猪肠粉档口面前,那位越妇放下手上的纸碟,瞪着金鱼大眼定定的瞧着我,仿佛我脸上贴了金银、或者五官变成了猪八戒?原想买点肠粉充饥,因她的无礼惹起不快,转身起步、不意耳边响起了一句久违的越语称呼:“安海!”。我是家中老大、越南朋友或同事均尊称我“安海”、Anh Hai 即大哥之意。
我惊讶中寻声转首,正是卖肠粉的越妇,她堆起笑、眉梢眼角的皱纹漾开,金鱼眼射出一抹光芒,在那张笑吟吟的脸蛋前我的不快已遁走,代之而起的是不解和迷惑。
“真的是安海啊,你忘了我是谁?我是翠娥呀!”
很美的名字,但如何能从这张被无情岁月的魔手:雕刻到揉搓成一堆的苍老颜容,去令我记起她是谁呢?看见我茫然不解的神色,她脱口说:“大叻市叹息湖边的翠娥就是我!”
时光开着倒车从我记忆深处、奔回半世纪前,为了逃避充当美军炮灰的去做越战的牺牲品,我更改身份离开南越首都西贡,前往三百公里外的观光胜地山城大叻,投靠张忠智神父开办的一所天主教小学“圣文山书院”,滥竽充数的做起老师。
宁静的山居让我忘却红尘外的隆隆炮弹声,大叻犹如蓬莱仙境,春香湖、皇陵、鹅芽大瀑布、军校草坪等引人入胜的美景,几乎都有我不少足迹。每日黄昏散步、徜徉于湖光山色怀抱中,犹似我已溶入了山光水色里,真是其乐融融。
学生告诉我、在离开市区约十公里处,靠近保大皇族的陵墓附近,有个叹息湖,当听到湖的伤感名字我已被深深吸引。问明了路程方向,在那个樱花怒放的春末假期,我独自去到了叹息湖。比起妩媚的春香湖,这个凄凉气氛弥漫的小湖让人心情沉重。四周被松树重重围绕,山风拂掠、果然传来幽怨哀绝的声声叹息。宛若有许多肉眼难见的魂魄在你身前倾诉,胆小的人往往竖起毛孔落荒而逃。我对荒野异闻鬼孤怪事向来不信,因此沿湖漫步,细细聆听松涛鸟语;耳旁叹息声时续时断,遥遥吹拂的冷风中,却偶然掇拾几声悲哭,令我顿生好奇。
大叻山城海拔几千公尺,群峦起伏,山岚云雾终日游移;叹息湖藏在群峰中一处平原,白云随手可抓,有时贴面冰凉。我追踪着若有似无的哭声,在云块飘移中忽然一阵清风吹过,眼前一亮、有位穿着越南传统“奥袋”长衫的少女,白衣如雪的站在湖畔。婀娜身姿散发出女性天然的美感,我犹若被磁铁吸引的一枚小钉子,不由自主的脚步竟向着她趋前,好像到叹息湖就被预设着要遇见她?
许是我粗重的脚步,或者是松针被踏碎前的吱嗄声,白衫少女回眸,那双精灵光芒的金鱼眼溢着泪珠。我的心顿时如滚水沸腾着,忐忑不安的跳动,望向她那张哀恸凄绝的容颜,真想不顾一切的上前为她拭去眼颊的泪痕,我却矛盾的不敢造次。趋近时点点头,掏出手巾无言的递过去,她摇摇首没有伸手接,就让那方手巾尴尬的停在空中招展。
“小姐、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我的口齿忽然笨拙,有点含糊的打破沉默,没想到她“哇”的一声让山洪倾泻,将内心悲苦尽情倒出。在我这个陌生者前、她似乎在水上抓到一根浮木,我却被她的哭声吓到手足无措,深悔不该多事与唐突,忙是帮不上竟惹到姑娘悲从中来。
“小姐、什么困难的事情都能解决,请你别哭吧!”
“不、没有谁能解决,他死了……..呜!”她猛力摇首,提高声浪有点凶的吼着,我仿佛是凶手害死了她口中的他。她挪移几步、伸手接过那块仍握在我
手指的方巾,拭着泪水、忽然在木椅坐下;我怯怯的靠近她,在椅的另
一端也就坐。轻声的对她说:
“人死不能复生、请你要节哀!”
她投过一抹冷然的眼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没来由的反问我:“你
知不知道这个湖为什么叫做叹息湖?”
我茫然的摇摇头,早已问过学生们,大家都无法说出原因。想不到这位在湖边哭过又叹息的少女会如此问我,心中一喜、竟忘了她先前悲切,她启口说: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恋人,因为家庭反对她们的婚姻,在无法可想的环境里,双双来到湖边。她们对着四周的青山跪拜天地,结为夫妻,便恩爱缠绵的度过几天灵肉交流的生活后,一起投湖自杀。
男的在冰冷湖水中挣扎,竟游上岸;女的沉尸湖底,大概死不瞑目?从此游人便经常会听到一声声哀怨的叹息声,故此人们就把这个无名的小湖称做叹息湖。”她瞪我一眼,又狠狠的说:“男人都没良心,专门欺骗女人,他自己死了,叫我怎么办?”
“他也来投湖?”我自作聪明的猜想着她口中的他是如何丧命的。
“不是、他前周驾飞机轰炸顺化城外时,被越共的火箭炮击落飞机而牺牲了。”
“那他是为国捐躯,不是故意弃你不顾,起码没骗你。”我好心的试图去安慰眼这位可人儿。
她抬头瞄我一眼,幽怨的说:“我们原定在下个月尾结婚,我父母始终反对我嫁给军人,我一直都怪父母,现在明白已太迟了。”
还没成亲、男友捐驱,她总算不是寡妇,是不幸中的大幸,为何说“太迟了”。我被她的话弄糊涂了,忍不住唐突佳人,率直问她:
“小姐、你还没嫁、他已亡故,实在是无缘呵!”
“我叫翠娥、在大叻女大师资系就读,他是我芳邻,青梅竹马,我们私订终身后,我已是他的人。现在有两个月身孕,他才弃我而走,叫我怎么办?除了投湖、我已无路可走。”她的话讲完、泪珠又滚落。
但凡自尽者都在一念之间,那刻冲动消失后,寻死的想法必然有变。我无意间的出现,像是一段水里的浮木在她溺毙前给抓紧;经过倾谈,我善意为她提出几种解决方案。当时几乎想扮演她的情郎去蒙骗她的双亲,幸好荒谬的念头才掠过便触及手指上的订婚戒指,终究没将那个怪想法讲出来
乌云飘移而化成鹅毛雨丝,我撑着伞陪翠娥离开叹息湖,回返红尘、我不放心的送她回家。后来我们成了朋友,我安排学校的同事老郭和她认识。老郭被她楚楚动人的风姿以及无奈的故事感动,居然像我般傻得见义勇为,荒谬如我,为翠娥日渐挺大的肚子负起“经手人”的角色。至于有没有弄假成真而结为夫妻?我因转到芽庄市而和她失去了连络,从此再无音讯,她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兵燹连年及至越战结束,我没有再回去大叻山城,擦身而过的人和事也无法都存进记忆。岁月在指罅里分秒奔驰、寂静流逝、悠悠数十载。没想到天涯海角外再能与故人重逢。令我吃惊万分的是当年娇艳婀娜的红颜,怎么会变成眼前老态毕呈的婆娘?在迷茫的时光燧道中我回返现实,为了证实翠娥确是当年那位故人,我问她:
“我以前介绍给你的那位朋友叫什么呢?”
“阿郭、他是好人,我后来做了他的妻子,一九六八年越共总进攻、不幸他被美军飞机投弹炸死了。相命先生批我的八字说是克夫命,逃难时沉船,我最后的丈夫和儿子也丧身大海。唉!早知道一生如此苦命,那年投入叹息湖,安海!你今天就不会见到我了。你胖了、样子竟没变我才认得出来,真难相信呢,转眼几十年了。”她的叹息声仍似当年那般哀怨。
果然是她,真的是翠娥,不然她不可能说出那位我介绍的同事老郭。她弄好热腾腾的肠粉递给我,我像在梦里般追忆已逝的青春。残酷的光阴太也无情,红粉佳人今何在呢?迎面风姿撩人的越南少女姗姗行至,竟然是翠娥的翻版,她穿越式长衫、如雪白衣飘飘,笑吟吟的搂着翠娥,经翠娥介绍,她赶紧对我颔首、礼貌的称我叔叔。
“是我小女儿雪芬,在墨尔本大学读律科。”
“她就像你以前的模样,我脑里的翠娥是她不是你啊!”我微笑着说。
“安海、您好命不知苦命人的生活,现在总算安定了。我一直希望能再遇到您,无论怎么说,您都是我的救命恩人,有空时、请大嫂来我家,好吗?”
我向她要了地址和电话,在锣鼓声中和她母女挥手,耳际仿佛响起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踩踏着鞭炮散落的红碎纸,依稀是枯黄的松枝,叹息湖在千山万水外低沉的叹息声竟在我耳际回旋,久久不散、、、、、、、、。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墨尔本初夏于无相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