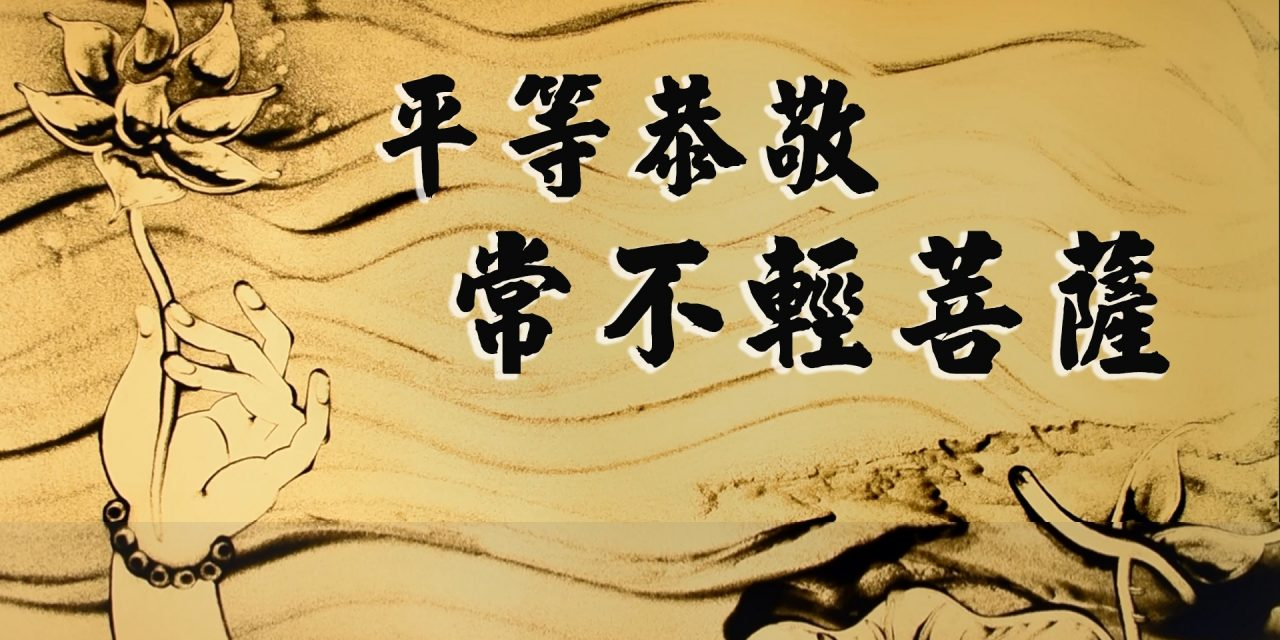明雪第一天上斑,九龙厂的全部眼睛都给她的妩媚照到特别亮丽,机器车间平白多了一位艳如彩蝶的女子穿插飘飞,整个工地格外显得生气蓬勃。弟兄们都为了自己赞成经理聘请秘书而感到快乐,明雪的有礼和常时挂在脸颊的笑涡,在元波为她逐一介绍厂里的弟兄们时,几乎立即赢到了他们的友谊。元波看到如此,心里是比谁也来得高兴。唯一使他不安的,是没多久之后,弟兄们似乎比往常更勤快的出入于文房里;而到文房来,十有八九并非找他。明雪一视同仁的用她可亲动人的姿容,耐心的为弟兄们解决些公文或者是些并不必要的对答,她愉快的认为是她本份内的职责。在没影响到生产进度的情况下,元波视而不见,没有把那份不安显露。
年关迫近,市面上摆卖年货的摊档比往年多,庙宇香火依然鼎盛,元波抽空陪母亲到二府庙拜神,福德正神供桌上除了各类三牲外,再没有整只红烧乳猪了。在回家途中,母亲对他说:
“今年是越共来的第一年,本头公就莫烧猪食了,以后,惊连三牲鸡鸭也莫人拜。”
“妈,人连饭也莫汤食,神明只好也跟著饿啦!”(莫汤食即没得食)
“神佛有灵,为什么要给越共打胜仗?”
“越共是不信神明的,所以神佛也就对伊莫法度。”
回到二弟的家里,他母亲下了车、元波辞别了母亲,忙著又赶回工厂里去。
明雪看到他,笑盈盈的说:
“波兄,原料已经用完了,工业厅要过了年才再办理,你试和他们谈谈。”
“谢谢你,我明天会去走一趟。”
“今天想你帮忙。”
“什么事?”
明雪用手指进工地,轻声而略带羞涩的说:
“好几人都要送我回家,我全推了,走去坐巴士,他们又跟著来,你可否送我?”
“好的,也顺路。”他说完,心里有点忐忑,借故走进工场,原料用罄后,弟兄们没事可做。三五成群的聚了好几堆,有的在对奕,有的在玩桥牌,有的抽著烟在闲聊。阮拾和元浪以及另外七、八人围著 一座车床,在看平摆在车床上边的越文解放报;阮拾嘻哈哈大笑,瞄见元波,立即向他招手。元波走近,望向报纸上的标题,居然是报导九龙厂超额完成指标,提前把产品送到工业厅属下的湄江厂,在全郡生产竞赛中,荣获亚军云云。
“经理,我们该庆祝这次的胜利呵!”阮拾开玩笑的说。
元波也笑了,他们都明白,前后送去一千对产品,根据合同是要三千对才算是完成指标,照理论他们是该罚的,天下再没比这更荒唐的了。他们居然是亚军的得主?那么、其馀没名的大小工厂,生产情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整张报纸所刊登的有那一条属于忠实的消息呢?为什么,为什么新闻部要这样骗读者?全南方唯一的报纸,每天就如此将谎言向人民输送,目的是要全民在新闻上有个错觉,然后去相信领导的是十全十美的政府吗?难道,他们连纸包不住火的这点道理也不懂吗?元波心底勾起了连串的问号,却不敢把那些疑问向人提出。
他已明白了阮拾为什么看了内容会发笑,谁能不笑啊?他不知道中央的头头们是否看多了这种利好新闻后,会真的相信他们治理的国家日益进步起飞强盛?社会主义的天堂指日可待,没有人会知道。元波看到的是,九龙工厂在重重关卡的剥削下挣扎求存,讽剌的是剥削者是来自各级有关的政权人物,他真的对“解放”这个词语感到了害怕。南越人民支持盼望的“解放”是如斯的一层新枷锁和一道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网,把一千七百多万的南方人民通通网罗进去。
“没原料,大家打扫清洁后,可以下班。”元波愕了一会儿才决定让弟兄们回家,那些埋头对奕的和玩牌的并没有立即散去,无事的旁观者三三两两的推了车出厂。明雪也已把一些公文打好字,该忙的都已做妥,元波再进来时,看到她也没事可做,便对她说:
“走吧!你把门关好,我推车在门前等你。”
明雪拿起手袋,就去拉门,出到前门时,三、四个早先要送他的弟兄都在那里,她正在不知所措,元波恰恰把车推到她身旁。弟兄们笑著和他招呼,也笑著和明雪点头,然后目送明雪坐上经理的车后座,并意外的看到明雪亲热的将右手伸出去搂抱他的腰,车开动后,她还回过头来,浅笑盈盈的向他们“拜拜”。
元波的粗腰感到一紧,柔柔软软的一条似蛇的手臂已缠上去,背部阵阵温热。一团棉花似的肌肤隔著衣服贴伏轻磨。在机车的颠簸中,舒服感升自背脊,往富林区的路伸延,他幌动里竟盼望这是一程没有终点的奔驰。
到达后,明雪大方自然的邀请他进家喝茶,元波的后背腰围却仍然觉到了有股温热的柔软在磨擦;他腼腆的回了些礼貌的话,就急忙的倒转方向,迎进凉风里。
踏进家门,本想把送明雪的事和报纸对九龙工厂的夸大消息告诉婉冰,但一眼看到阿美姐妹在忙碌的从小楼传递下他的书籍。匆匆上楼,瞥见婉冰在书架上也正把一堆堆的图书拿下来,他要讲的话一下子都飞走了,愕然的开口问:
“喂!阿冰、你在干什么?”
“搬出门外丢啊!”
“你疯了,我的书要拿去丢?”
婉冰转身面对他,指指手上的王云五字典说:
“你不知道,他们发动个什么扫除美伪文化的战役,喇叭今早就吵到现在;除了这类字典和医药典籍外,几乎都是要丢掉的了。”
“书有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明白?”元波颓然的蹲下来,抚摸楼板上那堆书籍,拿上几本又放下,他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十年来却陆续的收藏著一些他喜爱的书册;婉冰也是个喜欢阅读的女人,书竟是夫妇两人唯一的共同嗜好。两大柜连著木架上的书,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古典文学名著,杂文、散文集,经济政治的,哲学宗教,人文地理历史等。也有些言情小说,近千册的平装精装,每册都盖上了个红图章,写著购买日期,有的看过,有的买回来就藏到如今,还没翻动。
他不敢想像,这些与世无争的精神粮食,在越共统治下,竟要给拿去焚烧。距秦朝二千一百多年后,在交趾之国,在文明的廿世纪七十年代。嬴政的焚书会重演,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元波想不通是马克思的著作里是否偷抄了秦皇的治国之道?还是嬴政暴君比老马更先发明了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才会有那么巧合的共同点呵!
“不必想太多了,认命算啦!”婉冰倒想得很明智,语气轻松似的安慰丈夫。
“没法哟!留下有麻烦,都由你包办吧!我真的不忍心。”元波从书堆里站起来,跑上二楼,鞋也不脱,和衣躺在床上。心底有根针似的一下又一下的剌戳著,他想呼喊, 却张口无声,书籍何罪?书对他们有什么害处?书怎么会反动?他很伤心的为那些书呼冤,空气寂寂,所有的问号都留在他心里翻滚。
晚饭时他没有胃口,胡乱扒几口饭,话也不多说;闷闷的放下碗筷,也没心到门外纳凉,燃上根烟,独个儿又走上书房。站在书柜前,伤心而难过的瞧著两个空书柜。里边以前排挤到满满的书,如今只剩下几部中、越文字典,缩在一角,忍受著荒凉的空洞。
他一根烟接一根烟的吞云吐雾,想藉点尼古丁来麻醉脑中的一片乱,站也不顺眼,坐也难安静,负气的又下楼。走到前门铁闸边,在凌乱重叠的书堆旁蹲下,随手抽出一本看,是本《茶花女》。放到一边去,拿出另一本,是《梁任公全集》。然后是《圣经》、是《红楼梦》、是余光中的《莲的联想》、是《唐诗三百首》、《龙族诗刊》、《基度山恩仇纪》和《三国演义》。徐速的小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放到一旁去,再寻寻觅觅;又拿起本《老残游记》、移到另一边。又抚抚摸摸,拾起来看看,想想、扔回去,再拾起。每一本都应该没问题,放到一边去,越放越多,应该呈交的那堆越来越少。然后、心里早先翻滚的问题似乎飞走无踪,平静的走上楼,婉冰在灯下津津有味的读著金庸的《鹿鼎记》,他笑著说:
“你把两柜书都搬下去丢,自已竟偷偷的收起韦小宝,该当何罪?”
“我今晚不睡要读完它,明天他们来要书才交出去。”
“以后呢?”
“只好找些共产党国家出版的东西看啦!”
“怕没味道呢!我试读俄国的翻译著作和大陆的一些小说,全是八股的宣传东西,引不起读书的欲望来。”
婉冰放下书,凝望著丈夫说:“想不到越共一来,咱们连看书的自由也没有了。”
“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不过都会慢慢的让我们看到了。你不睡,我就不陪你了。”
婉冰又低下头去追读小说,元波躺上床,睁大眼睛望著蚊帐顶的图案花纹,脑里来来回回的都是太太刚才的一句话:
“越共一来,我们连看书的自由也没有了。”
不眠的夜,好寂寞难挨的长夜啊、、、、、、、
元波没精神,但还是撑著先到工业厅,“同志”们已不办公了,忙著打扫布置,准备过新年,原料只好等到过年后才可以解决。转到银行,好多人,他在队伍里一站,排队的时间总走得像蜗牛,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以前在《今日世界》那本杂志上看到一幅漫画;那条长龙队伍排著等分配食油,轮到漫画内主人公时,油恰巧的刚分完,他哭丧著脸的可怜表情,入木三分的竟深印在记忆里。当时他并不完全相信,想当然的认为不过是美国的反共八股;今天奇怪的浮现那张漫画,他竟立即在心中接受了,那是写实的作品。队伍移动,终于轮到他了。
三十七位弟兄年关倚靠的薪俸二千八百多元,出纳员脸无表情的告诉他,银行的现金发完了,明天再来吧。
元波在银行里转了一圈,希望能找到一面镜,他很想照照自已,看看脸上的反应像不像那漫画的主人公?可惜,镜架挂出来的是胡老头子的羊相(胡志明留著山羊胡须的照片),他只好走出这家郡属的人民银行。
门外,见到海哥,真是大喜过望的事。元波把领不到钱的事对他说了,厂长是很讲义气的,一拍胸口、想都没多想,就答应到他的商店里先取二千多元借给九龙厂过关。两个人沿著同一方向开慢车走,半小时后就双双停在林沧海的商铺前,元波看到那堆人又排长队在等购咖啡粉;心里总算明白了,门市收入都是现款,难怪他毫没犹豫的可以帮九龙厂的大忙。
拿到钱,也顺手接过一张海哥写好的送礼名单,元波打开一瞄,咦!这次连那名银行的出纳员也榜上有名,他指著那个木无表情的名字,抬头看林沧海:
“这个家伙也要送他?”
“早就该送了,今天的教训你还没醒悟?”
“你是说他故意为难?”
“不错、银行经理要送礼,小职员直接或间接和我们有关系的都不能免。”林沧海抽出根三五牌的香烟,把烟抛过去给元波。
“这样,不是比阮文绍的政权更糟吗?”
“对呵!老鼠跌落米仓能不吃吗?”
“海哥,如此大小通吃,米仓的米很快会给吃光了。人民怎么办?”
“死两个算一双,人民!人民只是招牌啊!傻瓜。”林沧海把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往上轻轻一推,望著元波滔滔的往下讲:“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公安、人民法庭、人民银行、人民议会、人民医院,那一样不挂上‘人民’这块大招牌?只有殡仪馆,监狱,坟场,劳改营还没有看到他们用人民这块美丽动人的名词。你告诉我有那一样是属于可怜的‘人民’的?”
“你对,用上人民做招牌的都没有人民的份,不用人民做招牌的劳改营,坟场,殡仪馆,监狱,经济区,却是真真正正留给人民的。唉!我怎么要经你讲才想到呢?”
“这番话,都飞了。回去发薪吧!以后、千万别再提起了。”
“我知道、人民现在是连言论的自由也丧失了。再见!海哥。”
元波回到九龙工厂,弟兄们雀跃的跑出厂房欢迎他,他笑著把钱交给明雪;然后告诉他们在银行的麻烦,大家愤愤不平。但对于原料仍没著落一事,倒都在担心九龙是否能继续生产?他们已很明白了工人当家作主是种什么真相,党的严密组织网络;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在整个社会结构层次上,密密麻麻围绕囚困著:工资、原料、运输、生产数量、银行、行政、职业、言论、甚至宗教,都有一双无形的手伸进去,左右控制著,强迫依照党的指示运转思考。
不论这种运转是多么不合逻辑和情理,多么阻碍社会的进步及发展;人民的眼睛虽然很雪亮,但却无力变更或停止。因为人民除了眼睛还可以张望瞧看,舌头已经麻木,声带嘶哑;会写字的手不敢拿笔,敢动笔的手,敢发言的嘴,都早已不是“人民”了。所以、南越只有一份报纸,一个电视台和唯一的无线广播电台。
明雪很快的把钱分配进她早已计算好的工资信袋里,再交回给元波,然后分发给厂里的弟兄们,大家领到工资后各自星散,工厂也草草收工了。
元波再送明雪,她依然亲热的横抱他,到达时、她下了车,面对他,浅笑盈盈的说:
“进来喝杯茶,给你看张心的信。”
元波正准备转过车头,听到张心的消息,只好也下车,走下石级随她进屋。
“伯母呢?她还好吧?”
“她去女儿那边,晚上才回来,人还蛮壮健的。”明雪边说边倒杯冷茶,元波拉开木椅坐下,望著她。
“没有信、你是不进来的了,所以骗你。”她接下去自言自语,也拉了张椅子,靠近他。
“原来你也会顽皮,骗我进来什么事?”元波有点哭笑不得的感受,但已经来了、也唯有听其自然。
“我很闷,你为什么要避开我?”
元波心里一跳,急急的说:“没有啊!明雪,你怎么了?”
“张心要你照顾我,是不是?”她迫视著他,眼睛内在燃烧心中的火。
“是啊!我已经做了,也帮你找到工作。”
“除了这些,你从来就没有关心我了。”她忽然抽泣,泪水盈眶:“你有没有想过?张心也许今生都不会回来了,我怎么办?”
“总有希望,是不是?”
“我很年青,不甘心就这样的给岁月埋葬,你明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别想太多了。”元波手足无措,心慌而徬徨的瞧著她。
“为什么我要是张心的太太?波兄!你知不知道,我每次见到你后都要失眠。为什么上天要我认识你?要你成为张心的朋友。”明雪喃喃的把心中千回百转的念头尽情吐出来,像火般喷到元波一脸的热。他站起、明雪也推开椅子,出奇不意的伏倒在他身上。元波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想推开她,又不忍心出手。挣扎了好一回,终于将手改变了姿势,轻轻拍著她的肩背说:
“吉人天相,张心会回来的。”
明雪昂起头,泪痕满面,双手绕到他后背,紧紧地搂著。半闭起湿润的眼睫,微微张口迎著他,元波全身像给电流通过似的震憾。一阵幽香冲进鼻孔,他迷迷糊糊地在昏然中把头垂下去;一厘一分的迫向那张微开的口唇,眼中时而是婉冰时而是明雪,晃来晃去。明雪的样子在瞳孔里扩大,口几乎接触到那张湿唇时;猛然醒起她是朋友的妻子,那一念如电光的闪烁,刹那而逝。但已重重的击到了他脑里的细胞,及时下达了个不可造次的命令,制止了他进一步的荒唐行为。
明雪幌忽而沉醉的感觉里,飘飘的正在等待一个热烈的吻;半闭起眼睛已完全醉在这个期盼已久的时光中。灵识微醺里,神经细胞亢奋的迎接爱的甘露时,不意那个下垂的头忽然再度昂起,并且腰肢轻轻的被两只炙热的掌心推开。
“对不起,我要走了。”
“波兄!你怪我?”明雪失望的、幽怨的凝视他,眼睛犹如敝开的门窗,期待和美景一览无遗。
元波摇摇头,心中很意外的浮起少校夫人在陈兴道那家半公开的妓院里狂热的动作。越南女人对于贞操守节观念和中国人的想法是有距离,那么、少校夫人也许除了钱外,还有生理的要求?正如张心的太太,他有了这个念头后,先前略带对她的卑视,竟化作份深深的同情,但无论如何也止于同情吧了。他还保留了继承了中国文化里挥之不去摔之不走的仁义道德重重的枷锁;这些东西,又是明雪所不会理解的。
他再次挂上个笑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彬彬有礼的告别了明雪。
踏入家门,骤然想起那大堆的书籍,便急促的回身张望。铁闸边两堆凌乱重叠的书本已空空如也,一阵昏然、使他要按著楼梯的扶手拾级上楼。阿雯和明明在房里玩耍,见不到太太,他冲进书房,一眼望尽,两个空柜冷清的摆放著几本字典外,所有他另选出来的书,婉冰并没有再放回去。好像买了张彩票,把发财的希望都注满了,开彩后中奖的仍然不是他。
女儿拿了杯热茶进来,他急著追问:
“阿美,你妈咪呢?”
“妈咪和杨太去排队买沙糖和猪肉。”
“那些书呢?放在铁闸边的两堆书都去了哪里?”
“早上来了很多人,妈咪和他们讲,他们还上楼看,结果、要妈咪签字,书通通搬上车。爸爸,他们为什么要拿走你的书呢?”
“爸爸也不懂。”元波颓然的抚著女儿的秀发,眼前浮现的是一本又一本的书,有精装的古典文学,有平装的小说,有莎士比亚的译本,有余光中的诗集。晃来晃去,都化作纸灰,在空气里飘扬。焚书的景象是那么遥远的荒唐故事,又竟如斯迫真的是眼前事实。
元波脑里在那片飞扬的纸灰中变得空空白白,一如两个大书柜,把空荡的内脏撕开,存放的不再是书籍,而是冷冷的空气。
更多相关文章可查询此处。